Featured Faculty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Weinberg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s
Clinical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s; Executive Director of Kellogg's Dispute Resolu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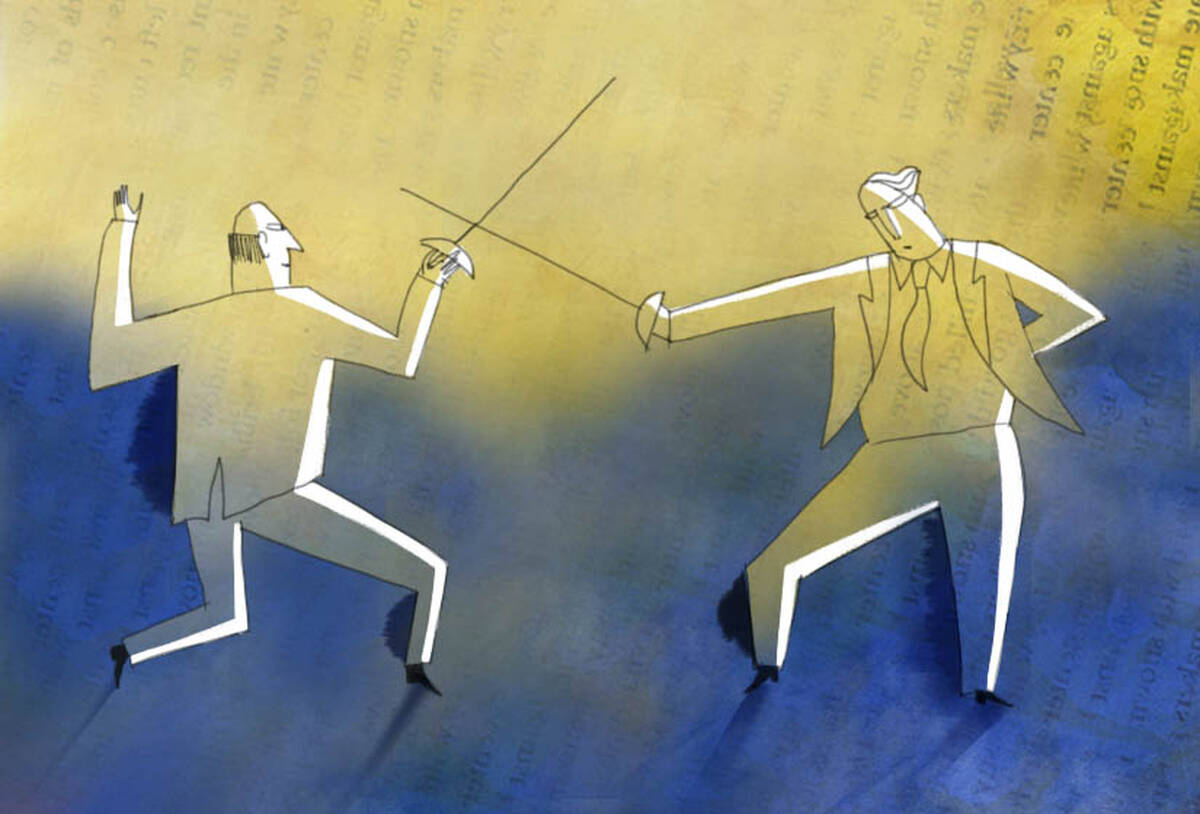
Yevgenia Nayberg
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已经习惯听到我们国家如何“极化”的说法,即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各自在自己的“回声室”怀抱着偏见或是“动机性推理”。专家学者们多年来陈述这个概念,次数之多让人听得不胜其烦。
然而真相或许比我们想像的更糟,而且极化现象并未完全反映出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党派仇恨。
一篇新论文指出,能够最贴切地描述美国政党冲突的术语是“政治宗派主义”,即政治团体基于道德认同而非共同理念或政策偏好结盟的倾向。
这篇论文的作者包括艾里·芬克尔和辛西娅·王,两人皆为凯洛格学院教授;詹姆斯·德鲁克曼和玛丽·麦格瑞,两人是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以及其他十一名来自不同学科的人。这些作者原本均计划参加一个由凯洛格学院的纠纷解决与研究中心和西北大学政策研究学院举办的会议,不料发生新冠病毒疫情,于是这群作者改而将他们的观点集中写成一篇论文。
“原因不仅仅是人们只信任或只认同他们自己这一方。”该中心主任王教授说道。“而是人们轻视另一方,视其为‘非我族类’并且更加不道德,这是一种存在威胁。这种群体外仇恨情绪的升高让我们相当震惊。”
有人可能称此现象为“部落主义”。不过部落主义是基于亲属关系的隐喻。作者认为,更适当的隐喻可能是几近分裂的鸿沟,在历史上分裂宗教派别,例如将逊尼派从什叶派分开,或是将新教从天主教分离。于是“宗派主义”一词应运而生。
重点不在于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信奉的理念是否源自于宗教,而在于美国现今政治认同的作用就仿佛是一种宗教认同。“对方不仅仅是错的,而且是邪恶的。我们这一方不够纯洁的人都是叛教者。”芬克尔说道。
这个重要概念来自于多项横跨许多学科、框架和结构的研究,而它们也都各有自己强调的主张与研究结果。
“从实际意义上讲,极化不是问题所在。”芬克尔说道。“政党之间清楚而且明确表达分歧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美国人对于对方政党的仇视心理更多时候是基于像宗教一样的社会认同感,而不是基于关于政策的实际分歧。”
研究人员认为,政治宗派主义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是“非我族类”,亦即将对手视为本质上与自己不同或异类的倾向。第二个要素是“厌恶”,亦即对于对方怀有强烈憎恶感和不信任感。第三个要素是“道德化”,亦即认为政治对手奸佞邪恶甚至是犯罪份子。
“这三者的结合使得政治宗派主义的腐蚀性相当强。”王教授说道。“每一个因素各自具有负面影响,但三项并存时即产生有毒的政治宗派主义鸡尾酒。”
例如,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党派在基于信任的基础上或许仍能通过妥协或劝说来解决双方的政策分歧。但如果各方都将对方视为道德威胁,那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变成零和游戏。”,妥协似乎成了叛教,王教授说道。
美国政治的分裂当然不是新鲜事,也不总是坏事。一个健全的民主需要经常对各种想法提出质疑,同时两党制有时可能会掩盖深层的社会不平等。例如,在1870年代,政治上的妥协剥夺了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投票权。在1950年,一些政治学家担心美国极化的程度还不够,认为政治过于地方化,主张一个立场和国家纲领相左的两党制度能更好地为选民服务。
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党派外仇恨现在已经超过群体内的团结。此外,现今美国人的投票行为,出于蔑视对方比出于支持己方所产生的投票动力更强烈。
对此感到厌倦的公民或许会问:我们的政治怎么会变得这么毒?是否有可能将过去四年解释为偏离正轨?
遗憾的是,研究人员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在论文中指出,成因与趋势可以回溯到三十年前。
部分原因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已各自归属为超越政治的认同群体有关。这些“巨大认同”已变得几乎相互无法理解。研究显示每个群体对于对方都有很大的误解。研究人员指出,“共和党估计有32%的民主党人是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等所谓LGBT族群,而实际上是6%;民主党估计有38%的共和党人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而实际上是2%。”
这些认同感在媒体势力的对决环境下更加强化,研究人员指出这种现象的形成可以追溯到里根政府对“公平原则”政策的终止,该政策是在二战后为了减少广播中的偏见而制定的。在政府干预的数十年期间,里根政府项的这项措施产生了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福斯新闻以及MSNBC。而在过去十年中,由于脸书和推特将使用煽动性与道德化语言的帖子通过算法大力推送来提高“参与度”,在这样的推波助澜下更加强化了宗派主义。
研究人员指出,政治精英之间也存在着明显分歧的趋势,他们越来越依赖极端主义的捐助者,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及其追随者开始,往往凭借着“充满愤慨的道德言辞”来获得支持。
研究人员认为,其凄惨的后果是可以预料的:社会疏离加剧,公民信任和规范崩溃,以及一个妥协的民主,领导者听命于极端主义捐助者,他们对党派纯度的关心多于对实际选民的关心。
“双方党派各自产生一套自圆其说的一致的论述,由其自身经验来看均是不可撼动的真理。”芬克尔说道。“尽管两种论述的详细内容南辕北辙,但它们在提倡自己的信念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对方如此腐败,以致于我方如果固守长期以来维护美国民主的那套规范,便成了容易受骗的傻子。”
这些影响充分显现在美国对于新冠病毒的反应上。也许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当对方构成“存在威胁”时,政党的反应往往是将违反选举法、藐视制衡、甚至助长动乱等种种反民主行为合理化。
“随着近年来政治宗派主义情绪高涨,支持暴力手段也激增。”研究人员写道。
那么,作为决策者或公民,我们可以做什么来给美国的政治宗派主义降温?我们如何建立一个专注于想法而非无法弥合的认同感的政治文化?
“简短的答案是,一步一步慢慢来。没有立即见效的灵丹妙药。”王教授说道。
即使如此,研究人员依然提出若干可能的介入措施。例如,纠正我们对反对方群体的误解或许有助于减少敌意,而学着将关注重点放在政策细节而不是认同群体上或许能够让各党派对复杂性有更好的认识,并培养一种谦卑感。作者们指出,“致力于弥合分歧的公民、宗教和媒体组织的领导者可以利用上述策略来减少可能助长政治宗派主义的那些自以为是的正义。”
如何处理社交媒体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鼓励人们花时间去评估脸书或推特上各种说法的准确性?一个可能的策略是依靠众包方式来识别正确内容并通过算法奖励该内容,从而减少虚假不实或极度拥护己方党派利益的帖子和媒梗的传播。
消除来自最极端捐赠者提供巨额捐款的竞选募资改革可能有帮助;解决党派选区划分不公的情况则可能更加鼓励在想法方面的竞争。
另外有些策略或许可在个人身上奏效,比如和不同政治意识的人打交道时学着使用对方的某些道德语言。例如,自由派可从国土安全的角度来讨论戴口罩问题;保守派可从未来照顾贫穷美国人的角度讨论降低赤字问题。
“有时不同的语言框架或使用可能有强大的效果。”王说道。“当你面对平行现实时,你必须找出有效的方法跨越这道鸿沟进行沟通。”
研究人员希望他们对美国面临的挑战所做的重新构想,能激起学术界以及决策者开展有意义的讨论,或许甚至能进而采取行动。
“希望我们能获得很棒的反馈,其中一些介入措施能够得到测试或应用。”王教授说道。“但我们将此视为第一步,未来任重而道远。”
